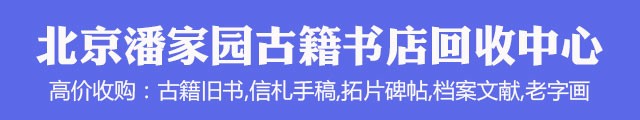关于读书,有几个误区似应破除。
误区一,求人开书单。就算被问者开出了书单,真正能认真读之者也不会多,因为未必合乎自己喜好。何况列书单者未读尽天下书何谈指点他人?钱穆曾说:清朝以后的书就不必读了,可清朝以前的书读得尽吗?此说不过钱老先生个人雅趣而已。
误区二,求问影响某人一生的书是哪本。此问往好了说,是个伪命题;往坏了说,实在幼稚。你若将此问题抛给钱锺书,他读了千万种书,让他从何谈起?他若说《事类赋注》,你可能一脸茫然,此书实在小众。影响人的书必然“积小流,方以成江海”。
误区三,读书就是学习吸收,悉数收入腹中,所谓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对于盲目照搬,柏拉图早做过判决:若有人只是对理念的二度模仿,必须将其逐出理想国。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不同意,提出了“模仿说”,从此模仿日盛,所谓“继承”“吸收”等观念为读书人所秉持。乃至大文豪T·S·艾略特也说诗人要从个性化中逃之夭夭,成为传统的一部分。难怪不少人醉心打探影响名人深的是哪本书,正是这种盲目崇拜心态作祟。
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·布鲁姆对传统,即所谓前人撰写的“伟大”的书持批判性姿态。1973年他出版了《影响的焦虑》,“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”。布鲁姆研究浪漫主义诗歌,出版过论布莱克、雪莱、叶芝等诗人的专著。在我们以往的传统教育和思维模式中,文学世界的后学往往是对前辈的学习和继承,但为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,其稳定的风格会发生嬗变?布鲁姆认为“迟到者”面临着前驱者的巨大影响,这既可以是激励和启发,也能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,让后来者陷入焦虑之中。于是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是对前驱作品的误读,以示叛逆和反抗,后来的诗人在面对前驱者的辉煌成就时,既渴望继承,又试图超越,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。这种焦虑促使诗人不断进行创新和突破,以摆脱前驱者的阴影。他们采用的策略就是通过误读和“偏离”前驱者的作品,来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解读和创新。
然而,前驱者的成就高山仰止,让后来者望而却步。为此,后来的诗人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挑战前驱者的,探索自己之路。他们也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,将前驱者作品的价值转化为自己的创作素材。中国历朝也有为创新而化用前人作品的例子。虽然过多化用会使境界不甚妙远宏大,但也不乏升华原作之功。即便诗人亦有“化用”之嫌。杜甫曾有诗云:“春水船如天上坐,老年花似雾中看。”其实南朝的释蕙标早有诗写在老杜之前:“舟如空里泛,人似镜中行。”初唐诗人沈佺期也曾写道:“人疑天上坐,鱼似镜中悬。”都是写行舟如在天际的意境,杜甫岂不是“剽窃”?但歌德言:“太阳底下本无新事。”点化前人词句而别开生面,本来就是自然之举。
王安石曾断言: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,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,正所谓“宋人生唐后,开辟真难为”,你让宋人如何写诗?王安石的一些名句也是点化前人诗句而来,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层”二句,化用的是李白诗句“总为浮云能蔽日,长安不见使人愁”。浮云给李白的感觉是愁,而王安石却不畏浮云、再攀高峰;黄庭坚的诗句“不只眼界阔多少,白鸟飞尽青天回”,化用的是李白诗“青天尽处没孤鸿”,李白写孤鸿远飞的状态,黄庭坚则巧妙地融入一种宽广的情怀。这类化用别有韵味,正是黄庭坚提倡的“点铁成金、夺胎换骨”之法,即“误读与创新”。
创作如此,读书亦当以故为新,面对珠玉在前的经典或正典,不应陷入盲目吸收的陷阱,而应在阅读中思辨性吸收,这样才能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(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)
来源:北京日报
作者: 王秋海